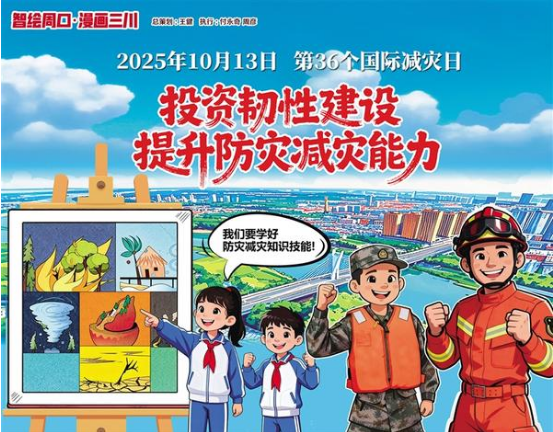英雄千古 氣貫長虹
◇司新國
或許是曾長期從事紀檢監察工作的緣故,在我的印象中,芷蘭是一個性格耿直、愛憎分明的人。她常著一襲旗袍,像是從民國時期走來的女子,溫婉間帶著幾分清冷。然而,芷蘭的文字是慷慨激昂的,讀之令人熱血沸騰。
我很喜歡芷蘭的作品,尤其是她的散文集《溫情與敬意》中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。在這篇長達萬言的散文力作里,芷蘭以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與歷史學者的嚴謹態度,以賀蘭山為引,以岳飛為魂,以實地尋訪為經緯,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追尋中,編織出一幅跨越八百年的歷史畫卷,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精神朝圣。
作為敘事起點,文章開篇即以“冀南新區人認為,《滿江紅》中的賀蘭山就是新區境內的賀蘭山,并對此堅信不疑”展開。不過,芷蘭并未陷入冀南新區的賀蘭山與寧夏賀蘭山孰是孰非之中,而是以“昔時古戰場,今日已成河北南部的活力之城……而賀蘭山,因岳飛而成為一處絕佳的人文景觀”表達了自己的立場。作者通過對賀蘭山地理位置的定位,勾連起岳飛一生的活動軌跡——從湯陰故里到太行戰場,從建康防線到朱仙鎮前線。這種空間敘事策略使文章既有微觀的具體性,又有宏觀的視野,為讀者構建了一個立體化的歷史框架。她引用《鄂國金佗稡編》等史料,記述岳飛出生時“有大禽若鵠、自東南來”的異象,又在敘述岳家軍戰績時精確到具體日期和兵力配置。這種對歷史細節的執著追求,為文學想象奠定了堅實的史實基礎,實現了歷史考據與文學想象的完美交融。她描寫岳飛在五岳祠立誓的場景:“面對五岳祠、面對‘神明’,岳飛所立的誓言,也是他畢生的追求。”寥寥數語,就讓一個滿懷報國熱忱的青年將領形象躍然紙上。
值得注意的是,作者對歷史空白處的合理想象。如寫岳飛與王彥的矛盾時,說“岳、王二人原本可以并肩作戰,甚至可以成為生死之交,只可惜岳飛年少氣盛”,這種基于人物性格的推演,既符合歷史邏輯,又豐富了敘事層次。她對岳飛形象的塑造,打破了傳統英雄敘事的單一維度,呈現出立體豐滿的人物特征。她既寫岳飛“凍死不拆屋,餓死不擄掠”的治軍嚴明,也寫他“文官不愛錢,武官不惜死”的政治理想;既寫他“三十功名塵與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豪情壯志,也寫他“欲將心事付瑤琴。知音少,弦斷有誰聽”的孤獨苦悶;既寫他四次從軍、四次北伐作為岳家軍主帥的英雄氣概,也寫他“年少氣盛”“擅自出戰”加之任性“致君臣之間嫌隙漸生”的性格弱點。尤為難得的是,芷蘭也揭示了岳飛作為普通人的一面:寫他“生平第一次覲見宋高宗趙構”時的忐忑;寫他收到十二道金牌時的無奈;寫他獄中面對秦檜等人的迫害,唯有“天日昭昭天日昭昭”八個字的絕望。這種辯證的人性化書寫方式,使岳飛從神壇走向人間,從符號回歸人性,讓高高在上的民族英雄有了溫度,更容易引起當代讀者的共鳴。
芷蘭還通過不同歷史人物的視角來豐富岳飛的形象。通過宗澤的賞識、張所的重用、趙構的猜忌、秦檜的陷害等多重復雜關系,全方位展現了岳飛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艱難處境。這種多角度敘事風格,使人物形象更豐滿真實。芷蘭作為女性作者對男性主導的戰爭題材的獨特詮釋,也豐富了歷史書寫的視角與深度。她沒有簡單重復岳飛“精忠報國”的主流敘事,而是關注英雄背后的情感世界。她寫岳飛:“他天性至孝,自北境紛擾,意欲再次從軍,又擔心老母妻兒在戰亂中難保周全。”這種對母親的孝順、對妻兒的牽掛、對家庭責任的糾結,展現了英雄背后的凡人情感;而寫到岳飛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時,“十年之力,廢于一旦”的痛惜,更是讓人感受到理想主義者面對現實政治的無力。
同時,芷蘭對岳飛悲劇的反思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:“岳飛被害僅僅是秦檜、張俊等人的責任嗎?事實上,南宋朝廷實行主和投降政策,最關鍵的人物不是秦檜,而是宋高宗趙構。”這種突破傳統忠奸對立簡單模式的制度性思考,揭示了專制皇權下忠臣良將的普遍困境。作者對權力異化和趙構的心理分析也尤為精彩:“站在金國面前的趙構,是小心翼翼、瑟瑟發抖、可憐巴巴的‘臣構’,為了議和不惜任何代價,可以割地賠款,可以任由金國的使臣謾罵羞辱……”“高宗最忌諱誰提起北伐或者迎二圣還朝,若父兄歸來,何以自處?”她描寫趙構從“慷慨請行”的皇子到“靴中置刀”的皇帝的蛻變過程:“沒有未來、沒有希望,趙構徹底成為一個沒有血性、沒有骨氣、自私膽怯的人。”揭示出絕對權力是如何腐蝕人性的。
作為一位深諳古典文學的作家,芷蘭特別擅長通過文本精讀揭示岳飛的精神世界。她將《滿江紅》與《五岳祠盟記》并置閱讀,視為“姊妹篇”。她注意到《滿江紅》中“臣子恨,何時滅”的預言性質:“一語成讖。此恨,是宗澤之恨,是岳飛之恨,也是陸游、辛棄疾之恨。”對《小重山》的解析更是入木三分:“《滿江紅》慷慨激昂,《小重山》明麗婉轉,雖然格調不同,但是不滿和議、反對投降、收復中原的主題永遠不變。”并引用龍榆生對《小重山》的評價:“一種激昂忠憤之氣,讀之使人慷慨。推其志,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”這種將文學作品置于精神框架中的解讀方式,使文本分析升華為價值傳承。從《五岳祠盟記》的意氣風發,到《滿江紅》的慷慨激昂,再到《小重山》的沉郁悲涼,這種創作軌跡的梳理,勾勒出一代名將的心路歷程,也折射出南宋初年的政治氣候。芷蘭還注意到文學作品在歷史傳承中的特別作用。她指出:“每到國難當頭、民族危亡之際,《滿江紅》是戰歌,‘還我河山’是口號、是旗幟。”這種對文學社會功能的認知,體現了作者開闊的文化視野。
文章最后一部分,芷蘭將筆觸轉向對岳飛記憶的尋訪。這是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最動人的部分,也是作者將個人生命體驗融入歷史敘事的嘗試。在太昊伏羲陵岳飛觀前,看到“浩然正氣”的門楣時,“我的心情突然激動起來,不能自已”。她引用《淮陽縣志》對“陳州大捷”的記載,還原岳飛與故鄉周口的歷史連接。這種地方史料的運用,不僅豐富了岳飛形象,也使宏大敘事落地為具體的地方記憶,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。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的深層意義,在于它不僅通過文學形式保存和傳遞了集體記憶,而且最終指向精神價值的當代傳承。芷蘭以飽含深情的筆觸,讓岳飛這位八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重新活在當代讀者心中。這種記憶傳承不是簡單的歷史復述,而是融合了考證、想象、批判與重構的創造性過程。正如芷蘭所說:“讀懂了岳飛,你就會明白,盡忠報國是血性,以身殉志偉丈夫,浩然正氣是中華民族歷經磨難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源泉。”這一論斷將歷史敘事升華為文化自信的表達,使文章具有了超越時空的思想價值。尤其是文章以西湖忠烈祠對聯作結,更見作者匠心:“奈何鐵馬金戈,僅爭得偏安局面;至今山光水色,猶照見一片丹心。”這種以文學意象收束全篇的手法,既保持了歷史思考的詩意,又留下了況味無窮的空間,實現了文學創作深層的文化使命。
芷蘭通過對岳飛精神的當代詮釋,為我們這個時代提供了一種精神坐標:在功名利祿之外,還有更崇高的價值值得追求;在現實考量之上,還有更永恒的精神需要堅守。這或許就是岳飛精神穿越時空、在八百年后依然能夠打動我們的根本原因。



ba31abde-b071-42ee-84bf-576d4b447441.jpg)